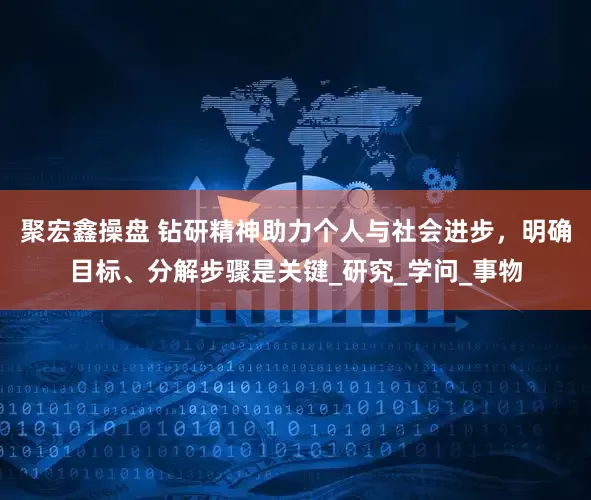“1952年10月13日23时鼎盛配资,‘就算剩下一把土,也要把高地留在身后!’”秦基伟在坑道口冲着团长喊完,掀开帘子钻进夜色。那句带着火药味的嘶吼,此后很长时间在前沿阵地回荡。
进入1952年,朝鲜战场线条已近乎静止,三八线周边布满壕沟、铁丝网,与其说是闪电战,不如说成了冷兵器时代的对峙。美军连同“联合国军”每天数十次火力侦察,志愿军则用小分队夜袭进行针尖对麦芒的反制,谁都想在谈判桌摆开前抢得一寸地形。

9月18日,志愿军发起秋季反击,先后拔掉三十余处连排火力点,美军第8集团军脸上挂不住。范佛里特走进板门店谈判帐篷时语气仍强硬,可回到汉城的司令部就盯上地图上那两个编号597.9与537.7的小山头——也就是日后被我们称作“上甘岭”的区域。
14日凌晨,美军炮口几乎同时喷火,一时间天被映成暗红。官方统计他们在战役初期的单日炮弹投入接近三万发,三角山一带土石被削下一层又一层。与威力同样惊人的,是密度:平均每平方米落弹六发,“地皮像开锅的沥青”,老兵后来这样形容。
火线另一端鼎盛配资,15军、12军早就在崖壁掏出纵横坑道。作战处的记录写道:敌人在地表寻找目标,我们在地下听炮弹落点;敌人上来冲锋,我们在侧壁打冷枪。不得不说,这套“土办法”把机械化军队逼得焦头烂额。范佛里特骂过一句:“他们像地鼠一样打仗。”

坑道生活并不好受。照明靠煤油灯,通风得用人力摇风机,炊事班不敢升火,只把炒面跟雪水拌一拌分发。即便如此,黄继光、孙占元们依旧轮番扑向敌堡垒。战役三十多天里,有名有姓记下牺牲的堵枪眼、抱炸药包英雄三十八人,作战科员晚点名时常常读到一半就哽住。
战场的烈度直接改变了飞机大炮的排布方式。美军为集中火力,将155毫米、203毫米重炮临时架到山路拐角,用直升机把炮弹往山上吊。一位美军观察员在日记里写道:“我们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,没想到在一个不起眼的山头重新开幕。”
43天,59次夺控,志愿军伤亡11529人,美军及其盟军损失超过两万五千。更致命的是士气,美第7师一名连长在回忆录里说:“只要听见山体里那种闷雷般的爆炸,我就知道中国人又从暗洞里冲出来了。”自此以后,第8集团军再未主动策划营级以上进攻。

军事行动的余波迅速传到板门店。11月中旬,谈判桌上,美方代表第一次没有要求修改停战区划分,只反复谈战俘问题。中国代表团内部文件里写道:“上甘岭后,对方让步的速度快得不合常理。”若用一句口语来概括:被打疼了,软下来了。
战斗当然也改变了参战部队。15军在回国检阅时,西安城门口的旗帜上写着“打出了中国志气”,那天秦基伟并没多说什么,只是摘下军帽朝士兵晃了晃。多年后他提起这段往事,仍用半开玩笑口吻:“从此别人见到15军,先打听你们是不是会挖洞。”
上甘岭同样塑造了一代军人的履历。李德生回忆书里写到,他在作战室端着半碗凉面听炮声,想不出办法时只剩一句话:“顶住!”这份“顶住”的履历,让他此后无论走到哪个军区,都被视作“能够在关键时刻死扛”的将领。

有人问:抗美援朝仗打了三年,战役级别十一场,为啥偏偏提到上甘岭就肃然起敬?其实答案并不复杂——它把前线对阵、谈判桌较量、装备差距、意志比拼统统浓缩在一座山头。规模不算最大,火力却最密集,时间不算最长,心理震撼却最深。
再过多少年,关于那段历史的电影可以有各种版本,但有一点不会变:山还在,弹坑犹在,当年的几把泥土里还掺着钢片、弹壳,静静说明了什么叫“咬着牙,也要守住最后一把土”。
启泰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