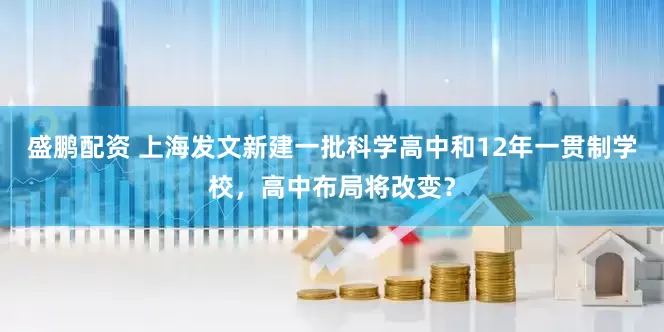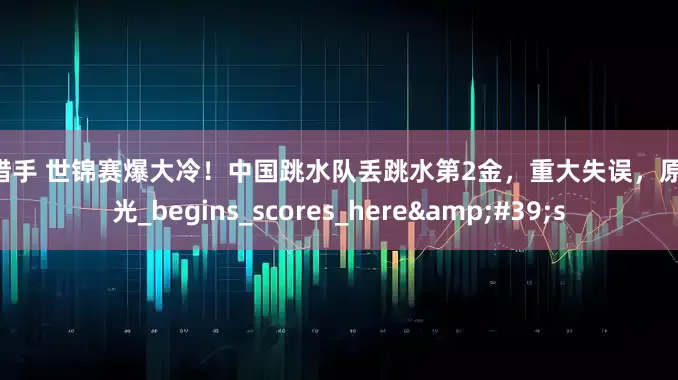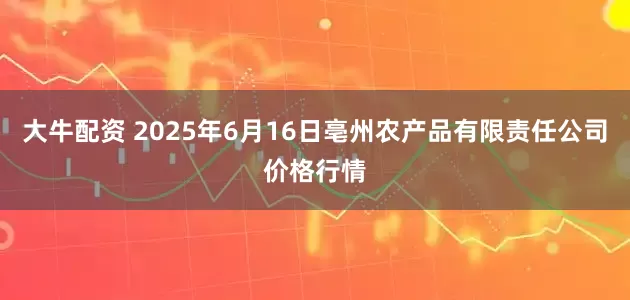“1976年1月31日夜里十点多无忧配,外头炸起来了——嘭嘭!”警卫员陈长江推开半掩的窗户,回头冲床上的毛主席喊了一句。
冬夜的勤政殿灯光昏黄,风吹窗棂抖动。屋里只有呼吸机轻轻作响,83岁的毛主席撑着枕头,脸色苍白却精神清醒。自1974年心肺负荷加重后,他很少说长话,今日却微微抬手示意陈长江靠近。
外头是京城春节惯有的热闹。普通百姓的爆竹声顺着红墙瓦脊滚进中南海,隔着院门,欢笑听得真切。往年,为了首长安全,警卫部队会主动让院里“静音”。这一次,毛主席开口了:“新年的炮仗,你们也放一点吧,屋子太冷清。”声音沙哑,却透着认真。

这一句请求把值班人员吓了一跳。老人家节俭是出了名的,连家里孩子寄来特产,他都照价付款寄回。何况这几年政治节奏紧绷,几乎没人敢在首长面前提“热闹”二字。
不得不说,陈长江心里五味杂陈:他跟着主席七八年无忧配,只见过老人嘱咐“别浪费”“别扰民”。突然要放鞭炮,像是想抓住什么。
鞭炮不好买,警卫员出了西门一路小跑到南长街小铺,掏出短缺的“红双囍”三挂、烟花两束。不到半小时,院墙边就“噼里啪啦”炸开。火光映红半片屋檐,老人侧头望,嘴角慢慢翘了起来。周福明小声说:“主席笑得真像回到韶山。”

许多人不知道,毛主席对春节始终有深厚感情。1900年代的湖南乡下,腊月二十四打糍粑、二十七杀年猪,孩子们抢着放“金竹炮”——他对这些细节记得极清楚。
1929年除夕,红四军在江西大柏地歇脚。刘士毅部尾随紧逼,粮弹紧张,毛主席还是让连部向乡亲借米、打欠条。那一夜,战士们端着南瓜稀饭照样给首长敬酒,毛主席放下碗说:“吃饱,明早打胜仗。”第二天果然大捷。旧部后来回忆:“那顿年夜饭比缴枪更暖。”
1930年初一攻占广昌,毛主席站在城墙上对干部笑:“在广昌过年,红军要红红火火。”他相信士气与年俗一样无忧配,都是人民战争必不可少的“燃料”。
再往后,1949年腊月二十九,党中央移驻北平香山。毛主席踩着残雪对周恩来说:“进城后第一件事,先让群众过年。”于是,解放军发出严令:进城部队不得扰民,商店照常营业,鞭炮不禁。北平老百姓第一次发现,这支队伍懂得尊重他们的年味。

建国后的春节,毛主席多半在家中或外事活动间穿插读书写稿。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初稿都与假日时光有关。他自己吃得很素,一碗腊八粥、一盘糯米蒸肉,极简。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,他干脆取消了家宴,对卫士说:“大家都紧巴,我怎么好意思吃得热闹?”
1976年的情形却完全不同。身体机能下降到需要吸氧维持,他走不了几步就气喘。连春节对外慰问电都是秘书代笔,他只是用铅笔在电稿旁简单勾画。医生劝他早点休息,他摇摇头:“许多年没听见院里有炮仗了,今天破个例。”
夜色里,爆竹尾火飞溅,映亮老人布满皱纹的面颊。那抹笑意,像极了湘江岸边少年抬头看焰火的样子。周福明握拳掩泪,他清楚地意识到: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在春节夜里陪主席听响。

时间很快推到了9月9日,清晨四点许,首长心跳骤停。护卫班里不少人回想起除夕夜的鞭炮声,才恍然——那是老人留给身边人的道别。有人私下感叹:“他让我们放炮,其实是想告诉大家,别为我难过,该怎么过年还怎么过。”
毛主席生前常说,“群众里头有真理。”连过春节,他也把人民的烟火气当成滋养斗志的力量。纵然在生命最后的冬夜,他依旧记挂工作人员能否感受到年味。他没有交代什么遗言,却用一串炮仗把关怀留在了空气里,炸得爽朗而清晰。
至今,每当农历腊月,值过那一班的老警卫都会想起那句嘶哑却温和的要求:“也弄一点鞭炮来。”它提醒我们:真正的伟大,不仅在于改天换地,更在于体贴人间最普通的欢喜。
启泰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