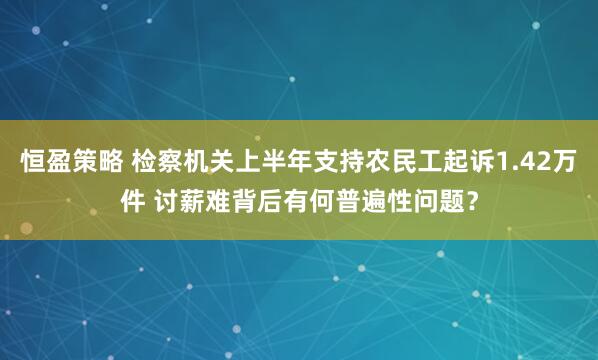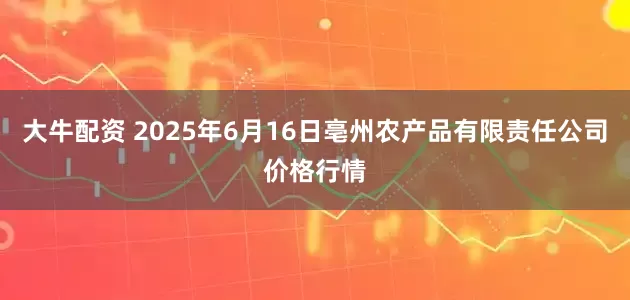“5月20日到了,准备下车吧。”2015年春末的一声提醒,把车厢里的人拉回现实。车窗外,熟悉的黄土高坡铺展开来国华通配资,李讷下意识扶了扶眼镜,神情瞬间变得郑重。这条“重走毛主席转战陕北路”的行程,她与丈夫王景清等人已计划许久,而真正回到延安,心头那股酸涩依旧猝不及防。
汽车先抵枣园。七十多年前,这里是父亲的住所与战时指挥部;如今,窑洞门口已排起长队。李讷并没有急着进屋,而是留意到墙角挂着一张老照片:年轻的毛主席轻轻托着襁褓中的她。她招呼王景清凑过来,“你看,原片还在。”语气轻,却透着难掩的温柔。短暂驻足后,她才随流动的人群走进窑洞,指尖掠过粗糙的土墙,灰尘裹着旧日气味,一起扑面而来。

傍晚,他们又去了杨家岭。路旁纪念品摊上,毛主席头像的帆布包、车挂、印章琳琅满目。李讷挑了两枚瓷像挂件,摆在手心,来回比量。同行的人笑问:“大小差别在哪?”她也笑,却没给答案。那一刻,她只是在用指尖确认父亲的轮廓——大号与小号,不过是岁月的两种刻度。
第二天中午,大型红色舞台剧《延安保育院》开演。剧中孩子们的朗诵声刚响起,她就绷紧了肩膀。1940年夏,她在延安中央医院呱呱坠地;六年间,枣园、杨家岭、王家坪是一方又一方小天地国华通配资,父亲的脚步、母亲的低语、窑洞外的风沙,都在剧里被重新点亮。演到孩子们躲进防空洞,李讷突然掩面,泪水止不住滑落。王景清悄悄把手放到她背上,轻声道:“出去透口气?”她点头,快步离席,观众席留下一排空椅。
离场后,她倚在剧场外的土墙上,望向舞台方向,却像在看另一个时空。脑海中,六岁那年撤离延安的雨夜重现——小韩阿姨把她放上战士的马背,雨披挡住湿冷,她却偷偷掀起一角,回头找父亲。昏暗中,只看见父亲背影在雨里晃动,手里那盏马灯像守夜的星。多年以后,她仍记得那道微光。

时间线倒回到1976年。父亲离世,举国悲恸。对外,她是主席之女;对内,她只是失去父亲的普通女儿。纪念堂落成仪式那天,她哭得几近脱力。姐姐李敏搂住她耳语:“咱们要自豪。”那句劝慰像钉子,一直留在她心口。也是那之后,她努力把悲痛折叠,投向平凡生活,带着儿子,辗转工作岗位,直至遇见王景清——对方当过主席警卫,两人有太多共同记忆,一拍即合。
1984年,她第一次隐身回韶山。冲着稻田和青山一声“爸爸国华通配资,我想你!”喊到破音,路边放牛娃愣在原地。那天,她挖了两把故乡土,用布包好,带回北京。朋友不解,她笑言:“这是家底。”朴素得像一把陈年棉被,却让她睡得踏实。

回到2015年行程。短暂休整后,她再次走进剧场。台上已演到孩子们唱《边区儿童团团歌》。“我们是新的少年先锋……”稚嫩歌声与她的幼年重叠,她没再离开。演出结束,灯亮起。有人认出她,小声感叹:“主席女儿也哭得厉害。”她听见了,微微颔首,没有解释。
次日一早,队伍去王家坪。那处军事首脑机关已被细心修复,桌椅摆设与1947年撤离时别无二致。李讷在地图前停住,手指在延安与西柏坡之间划出一段弧线,“当年就是这么走的。”声音平静,却带着久违的兴奋。她转身对身边的青年志愿者说:“你们现在看是一条旅游线路,当时可是真刀真枪的生死线。”青年点头,眼睛亮起来。
午后,他们驱车离开延安。车窗外,黄土峁峁此起彼伏。李讷望了许久,突然想起四岁那年父亲牵她进枣树林的情景。她问:“为什么革命?”父亲俯身,“为了让放羊的老人都能吃饱。”她又问:“天天有羊肉吗?”父亲笑:“等大家都吃上咱就有了。”七十五年过去,城镇里的火锅店遍地都是,她却更怀念那几颗带虫眼的青枣——那是战火下最甜的滋味。

车到延安市区,她掏出两个毛主席瓷像挂件,最终决定大的留给儿子,小的挂在卧室门后。王景清调侃:“舍不得分开?”她摆手:“大小不同,意义一样。”说罢把两件小物件贴在一起,让它们彼此作伴,像父亲与她,隔着时光,却始终并肩。
傍晚的光线正好,延河水面反射出金色波纹。李讷靠在座椅,合上双眼。同行的人以为她睡着,其实她在默背父亲那首《沁园春·雪》。词中“江山如此多娇”的尾句顺着心脉流过,她忽然觉得胸口不再沉重。故地重游没有结束悲伤,却让记忆重新开了窗。温暖的风,从窑洞深处吹来。
启泰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